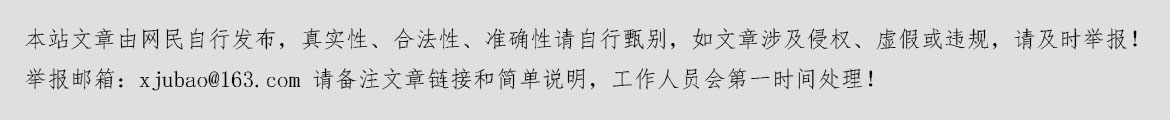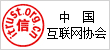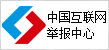福州信息社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生活百科、房产家居、投资理财、热点新闻、教育科研、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最可怕的打工仔:靠着一张好看的脸,毁了一个深圳富二代美女一生
2023-01-09 20:38:00
我老家在陕南偏僻的山村,村里的孩子初中基本就三条路可走:
学习好能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学习不好,但家里有点钱的,会花钱托人找门路上个中专卫校或者去技校学个一技之长。
像我这种家里又没钱自己又不是读书的料的,就早早跟着熟人四处打工,攒钱盖房,请媒人说媳妇。
2007年刚过完年,发小凌安峰就怂恿我和他一起到深圳进厂。我此前已经跟着村里人在南京小饭店后厨打了三年杂,钱没攒到还因为经常作息不规律落下个失眠的毛病。
而凌安峰则是跟着堂哥上了煤矿,煤矿虽然脏也危险,但好歹工资比饭店高多了,只是凌安峰好吃懒做还赌博成性,三年下来比我还穷。
两个不成器的人一拍即合,各自向家里要了路费就挤上了K448列车,奔向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城市。
火车凌晨四点到的罗湖火车站,外面一片漆黑还下着雨。走时老家大雪纷飞,到达深圳天气却湿热难耐。但凌安峰机灵,他很快看到很多人都在厕所换衣服,于是和我轮流看行李,顺着人流在厕所把各自穿了一个冬天的棉袄和毛裤脱下来。
南下之前,凌安峰听他一个亲戚说过,深圳石岩有个创维厂,大得望不到边,专门做电视机的。我们等到天亮后就找去石岩的车。公交车售票员大姐很没耐心,懒得指点我们在哪下车,把我们直接拉到了石岩万联超市门口。
一下车,我俩就被街道两边拥挤的人流惊呆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以至于在深圳很多年后,我们依然对当时宝石路上的人流拥挤心有余悸。
凌安峰本来就懒,在这样人生地不熟几乎寸步难行的时刻,他觉得我们这样走路找工厂简直是白日梦,便一头钻进路边一家叫“理想职业介绍所”的小门面不愿出来。
一个黑胖的中年人立刻上来拉住我们,一阵让人害怕的亲热问候扑面而来。他一边问一边讲自己当年出来打工如何和我们一样,如何不容易云云。很快他基本知道了我们的底细,让我们每人交400块钱,明天就能进创维厂上班,今晚住处他也能帮忙解决。
我们信以为真,赶紧交钱登记,生怕交慢了工作被人抢去了一样。收完钱押了证件后,他就把我们领到不远处一个旅馆,和里面那个大妈说了几句就回去了。大妈面无表情走过来说,每人每晚50块。没了身份证,我们有种任人摆布的无奈,又只好交钱住进那个房门都关不上的破旧标准间。
还好黑胖子没有食言,第二天用一辆冒着黑烟的面包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烂尾楼一样的厂房里。一群人坐在简陋的工作台上做电感,步骤倒挺简单,就是往磁环上绕铜线。一个大姐快速讲解了一遍,我们就都能操作了。
胖子说这就是给创维做的,我们的工资按计件算。我和凌安峰有点傻眼了,400块,进创维厂,这哪跟哪啊?越想心里越气,我们找黑胖子理论,让他退钱。
之前还插热情的黑胖子瞬间变脸,开始冷冰冰讲出来混要讲信用之类,说工作也介绍了,钱肯定是不能退,要是不想干,可以换工厂。也可以拿身份证走人,但没干满一个月,要交前面的伙食费交通费什么的。
无奈之下,我们决定换厂,黑胖子指使小弟气鼓鼓把我和凌安峰拉到另外一个厂,而且警告我们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不满意,交钱拿证走人。
车停在石龙仔工业区一个脏乱不堪的五金厂门口,黑胖子赶我们下车。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油污气味和震耳欲聋的机器嘈杂声同时从厂房里面涌出来,我和凌安峰想死的心都有了。
在那段生不如死的煎熬中,我们无意间发现,五金厂门口那个士多店里的女孩子,长得相当漂亮。青春躁动的我们,暂时忘记了工作的痛苦,并心照不宣地在那个五金厂坚持了下来。
我只敢偷看几眼,默默在心里幻想,但凌安峰脸皮厚,开始想尽办法接近那个女孩。凌安峰人长得帅,加上能说会道,很快就和女孩混熟了。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一个重大消息:那个女孩家里不仅有这间士多店,店后面那栋楼也是他家里的。
通过凌安峰,我对那个女孩了解越来越多。她叫张永香,云南昭通人,她父母很早来深圳打拼,渐渐站稳脚后,她和弟弟一起来到深圳。她真的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冷面美人,几乎厂里每个人下班都想往小店跑。
张永香虽然对高高帅帅、能言善辩的凌安峰评价不错,但那时绝对没有到喜欢的地步。山里娃凌安峰却丝毫不在意张永香态度如何,锲而不舍地进行着他的攻势。
在我们到深圳第二年的七夕,凌安峰策划了一场全厂瞩目的表白,最终在几乎五金厂全体好事男工的哄闹和祝福声中,张永香接受了他。
他们成了石龙仔工业区那一片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张永香的父母原本就是普普通通靠功力一点点打拼起来的暴发户,对生活没有太大的追求,对找女婿这件事也没有那么挑剔。他们只看着凌安峰一表人才,也会来事,就默许了这桩亲事。
有了张永香一家人的靠山,原本和我一样活得惶惶不可终日的落魄打工仔凌安峰,摇身一变突然成了当地人的女婿。他很快就住进了士多店后面的那栋楼,结束了和我一起哭丧着脸在模具下拣五金件的苦逼生涯。
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很快让凌安峰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最初他还经常热情邀请我去他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慢慢地,他似乎越来越不想看到我一身油污地出现在他面前。
原本就不喜欢五金厂这种肮脏嘈杂的环境,加上看着发小今非昔比的春风得意,我在干满黑胖子要求的时间后,默默离开了石龙仔。
一年后我再见凌安峰,是应他邀请去参加他们婚礼。志得意满的凌安峰,已经是老丈人入股的加工厂厂长。被安排坐在上席却唯唯诺诺的我,看着这个当年和我一起从山里走出来的伙伴,前途明朗,洞房花烛,那是多么令人妒忌的快意人生啊!
可能是因为凌安峰混得太好,我从五金厂辗转到形形色色的电子厂,一直混得不好的缘故吧,我们从原来无话不谈的发小变得联系越来越少,最终渐行渐远。
2013年底,张永香突然联系我,告诉我手下已经管控着两家工厂的凌安峰,竟然在外面找小三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不知所措。
那年他们的女儿已经快要上小学了,张永香为了家庭颜面,并没有和凌安峰大吵大闹。但她要强的父亲接受不了这个事,这个硬气了一辈子的老人,强忍怒火找女婿深谈了一次,要他悬崖勒马。
已经在商圈混得风生水起的凌安峰,在对他恩重如山的家人面前阳奉阴违,但一出门立马换一副嘴脸,变本加厉和小三鬼混,听说不只找了一个。
张永香不忍心年迈的父母为自己彻夜暗自流泪,来到我老家村里,想请公公婆婆出面,规劝丈夫回归家庭。因为凌安峰没有回来,语言有些不通,张永香找我帮忙给凌安峰不会说普通话的父母当“翻译”。
这么多年,凌安峰一直推推拖拖并没有带张永香回过几次深山老家,所以当猛然看到山沟里那个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的房子时,我和张永香都有些吃惊。
凌母脑子不怎么好,说几句话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让我们无法好好说话。凌父双耳都有些聋,我们又要说很大声音他才“啊”一声有所回应。面对着这两个文物一般的老人,我们的心都凉透了。
张永香拿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还借了我身上的现金,凑了一万多块全部留给老人,自己哭着走了出来。
送张永香去咸阳机场的路上,我们几乎都找不到话说。当年让我们一帮寂寞打工仔日思夜想的冷面美人,在生活和岁月面前,竟然变得那般弱不经风。
虽然凌安峰后来和我差不多断绝了联系,我深知我的话现在在他眼里还不如个屁,我还是专门打电话过去狠狠骂了他一顿。他还客套地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在石岩找工作的日子,嘻皮笑脸,让我有空过去一醉方休。
只是我没想到,那次竟然成了和张永香最后的诀别。
张永香回到深圳后,有种叫天天不应的绝望,回家又不敢表现出来,便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而生活以及她不堪重负的人生,也是从这里开始滑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2014年6月初的一天,张永香下班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通话竟然是那个小三,人家主动找上门了。打完这个屈辱的电话,张永香没法直接回家,怕父母看到自己失控的样子。
她一个人胡乱吃了点东西,喝了很多酒,边哭边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走。走到一个公园里面,张永香坐在躺椅上嚎啕大哭,也不知哭了多久,竟然昏昏沉沉睡去了。
等被叫醒过来,也不知道是半夜几点,椅子旁边围着一堆人。几名警察关切地看着她,警车上灯光闪烁,旁边一位警察正在把一个猥琐的流浪汉拷上警车……
张永香惊觉自己衣服被人动了,才发现自己身上盖的是一条毛巾被,警察小声告诉她:“别怕,别怕。”
原来这个无耻的流浪汉听到张永香一个人大哭时就躲在旁边盯着,直到张永香酒劲上来昏睡,他趁人之危侮辱了她……几个值夜班的人路过,看到这可怕的一幕直接报了警。
张永香大脑一片空白,接着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两天后,凌安峰看到报警人拍的张永香和流浪汉的照片后,恶狠狠地甩了两个字:离婚!
那两个字,是通过短信发的。张永香哭着打电话,凌安峰一个也没接。出事后,他一直躲着,连看都不愿再看一眼那个给了他一生荣华富贵的女人。
支撑张永香的最后一丝力量,被命运的稻草击溃,她默默流泪了一周,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当天,张永香吞下整瓶的药,等家人找到时,已经离开多时了,没人知道,最后的她,有多绝望。
2014年6月,我向公司请假,去参加张永香的葬礼。这个可怜的冷面美人,把她一生的热情都给了我发小凌安峰,而她自己生前最后几年,生活几乎已经支离破碎。所以,最后来送她的人,并不多。
这是我第二次去她家,上一次是参加张永香的婚礼。才不到八年过去,香消玉殒,物是人非,令人痛彻心扉。
葬礼从头到尾,张永香的丈夫,我的发小,陕南山沟里长大的穷小子凌安峰,那个最应该到场的人,那个靠着张永香才一步步混到今天风光无限的男人,始终没露一面。
一个人,竟然能无情无义到如此地步!
张永香的闺蜜咬着嘴唇流着泪说:“那个人才不会来呢,人家刚刚新提了亲事,正准备和新任未婚妻结婚度蜜月了!”
那恶狠狠的语气说得一字一顿,我想,她是想说给躺在地下的人听的。可惜,张永香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了——不听到这可恨的消息也算是好事,她也算彻底解脱了吧!
那几天,张家的大人小孩都小心翼翼,包括她生前的朋友们,也没人对我说过什么过激的话。
可是即使没有任何人责怪我,我还是比他们更加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轻易开口说话。因为那个毁了张永香的一生,让葬礼现场的每个人都恨之入骨的男人,是我的老乡兼同学,我们都来自陕南那个穷得可怕的山村。
这段如做梦一样的经历,是我不到三十年人生中,最压抑最沉重也最痛苦的旅程。从张家回来不到一周,我听张永香的闺蜜说,凌安峰举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
可怕的是,新娘并不是学姐知道的那个小三,听说是个更年轻的女生。